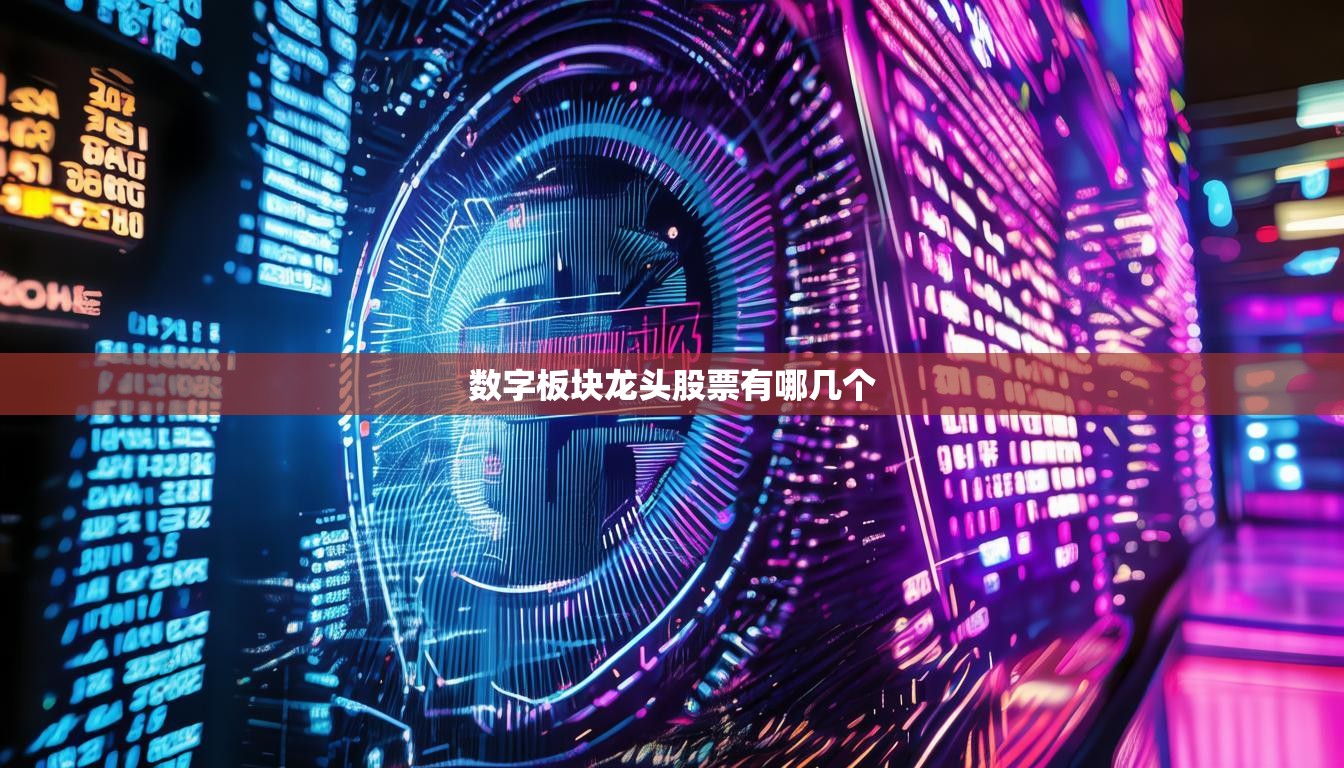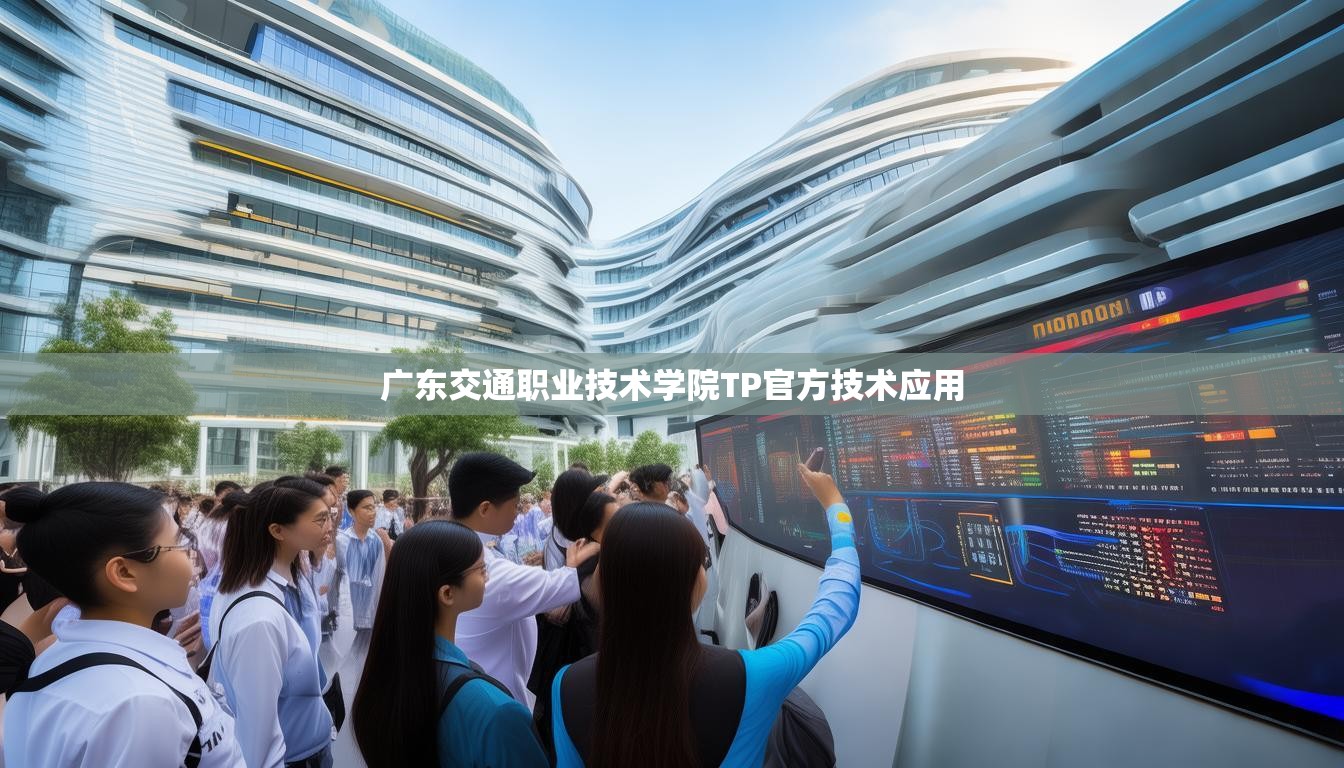追问“有什么用”,是人类进步的天性还是功利主义的陷阱?**
“这有什么用?”是一个再常见不过的问题,从孩子拆解玩具时家长的质问,到科研经费申请时评审委员会的考量,再到哲学课堂上学生对抽象理论的困惑,“有什么用”的追问几乎贯穿了人类认知的每一个层级,这个看似朴素的问题背后,却隐藏着认知的双重性:它既是推动实用技术发展的原始动力,也可能成为扼杀创造性思维的枷锁。
“有什么用”是文明的底层逻辑
人类对实用性的执着刻在基因里,早期智人选择打磨石器而非欣赏落日,是因为锋利的边缘能切割猎物;古埃及人研究几何学是为了丈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;甚至连看似“无用”的数学理论——如19世纪的非欧几何——最终也成为广义相对论的基石,历史上,无数曾被质疑“无用”的探索,都在时间沉淀中显现价值。

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的故事颇具代表性,当他的电磁实验被财政大臣质问“这有什么用”时,他回答:“一个新生婴儿有什么用?”几十年后,电动机和发电机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形态,这种延迟满足的“无用之用”,恰恰是基础科学的魅力。
功利主义视角的认知窄化
当“有什么用”异化为唯一标准时,危机随之而来,教育领域尤为明显:家长更愿投资编程班而非诗歌课,因为前者“能找到工作”;大学人文专业招生萎缩,而AI相关学科挤破门槛,这种工具理性思维正在压缩人类的认知维度。
古希腊人创办学院时,算术与音乐同属必修,因为他们深知逻辑与美育共同塑造完整人格,庄子笔下“无用之大树”的寓言,更揭示了超越功利的价值——那些无法被即时量化的思想、艺术和哲学,恰恰是抵御精神荒漠的根系。
在实用与超越间寻找平衡
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双重清醒:既要承认实用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策略,也要为“无用”保留生长空间,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,他的研究曾被同事嘲笑道:“这能发什么论文?”但正是这种看似没有明确目标的探索,最终革新了蛋白质分析技术。
或许,我们该用更开放的句式替代“有什么用”:“这可能会带来什么?”就像梵高的向日葵最初无人问津,却让后人看见燃烧的生命力;就像数学家哈代骄傲地宣称“我的研究毫无实用价值”,却被密码学奉为基石,人类文明的火种,往往诞生于那些敢于暂时放下“有用”执念的头脑中。
“有什么用”的答案,从来不是非黑即白,在温饱与战火尚未远离的现实世界,我们需要实用性解决方案;但若想触摸未来的轮廓,就必须保留一些“无用”的好奇,正如爱因斯坦所言:“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计算,也不是所有能计算的东西都有价值。”这种辩证认知,或许才是提问“有什么用”时最该获得的答案。
(全文约850字)